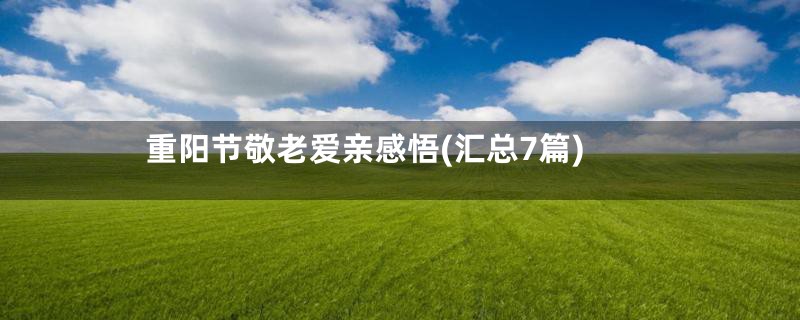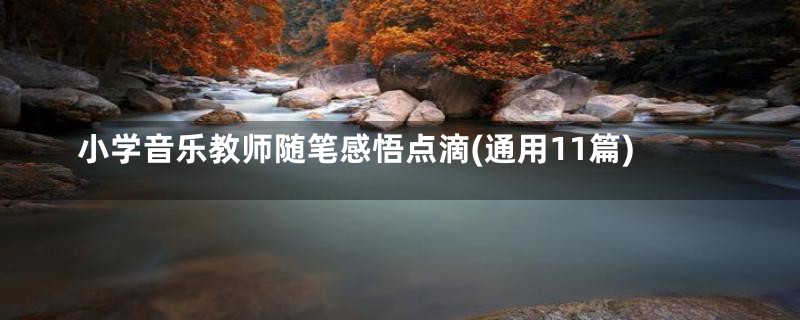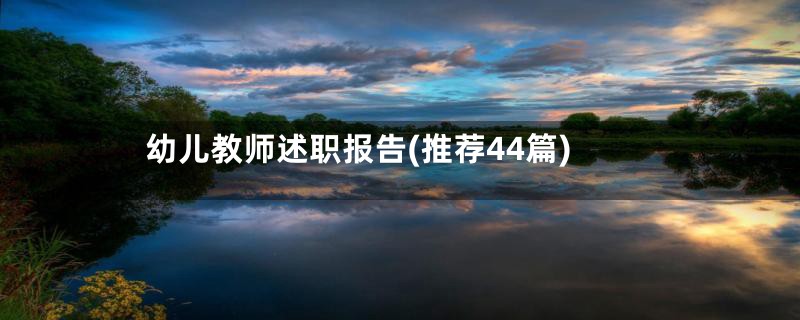人生感悟和哲学 第1篇
是一道道心灵的伤痕,
给我带来的,
是默默的抽泣,
我松懈了,
多想放弃,
用放弃来我的眼睛,
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得到解脱,
然而我没有放弃,
因为,
天空不总是蓝的,
有时也会变灰
花儿不总是鲜艳的,
有时也会枯萎。
失败犹如霜天雪地的冬天,
死一般沉静;
失败犹如孤苦伶仃的树枝,
断然没有一点生机;
但一切不代表结束,
而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寒冬的枯寂,
沉淀着春天的勃勃生机,
今天的忧伤,
孕育着明天的微笑。
做胜利的英雄容易,
做失败的英雄很难,
我们要有做失败英雄的勇气。
失败,
并不可怕,
没有永远的成功,
也没有永远的失败;
失败以后,
需要坚强的意志,
更需要坚定的信心,
记住,
失败乃成功的基石,
经历霜雪的果实会更甜。
(指导老师 郑冬华)
主题点评
失败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个让人不愿接纳的词汇。相反,“祝你成功”则是人们觉得动听、悦耳的声音。可是现实社会中,失败与成功总是如影随形,有成功就有失败,对于每个人来说总是有顺心或不如意的时候。
失败难道就是那样不好吗?显然不能这样认为。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事情都是相互转化的,相互依存的,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心态,理智地看待失败,或许透过失败的悲哀,你会发现失败对一个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财富,如果你正确面对失败,或许你会发现通向成功的路径。本文正是揭示了如何品味失败,正确地去感悟的道理,从中你还会发现,失败与成功同样能使人有所收获。
选材点评
本篇佳作选取了人类社会活动中常见的成功与失败这对矛盾中的失败进行构思写作,针对失败发出自己的感悟,针对失败抒发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同时,还应看到,选取了自由体诗的体裁来表达思想情感,似乎更能轻松灵动地揭示主题思想。
布局点评
本篇分了三个段落从不同角度来感悟失败蕴含的生活哲理。
第一段落,主要阐述了失败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上表面感觉,阐述了失败给人们带来的难以承受之痛。如“失败给我留下的是一道道心灵的伤痕,给我带来的是默默的抽泣……”等。
人生感悟和哲学 第2篇
关键词:灵感;迷狂说;妙悟说;悟
古今中外,许多天才型的作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到一种不受意志控制,不由自主的具有突发性与偶然性的创作力对文学创作的影响。由于这一神秘力量,才能使他们创造出瑰丽多彩、流传千古的艺术形象。这一神秘力量就是诗学领域通常说的灵感。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灵感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本文试图从中西灵感说的不同渊源入手,进行分析与比较,把握其内在的相同点与差异性。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并没有灵感这一概念,但是早在公元3世纪就有关于灵感的描述,陆机在其《文赋》里描述到:“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1](241页)“应感之会”就是他所谓的灵感的显现。而刘勰也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2](248―250页)这段话是刘勰对作家创作时的灵感状态的描述,在灵感到来时,各种意象就会不断地涌来,作家文思如泉涌,即所谓的“神思方运,万涂竟萌”。中国古代文论中对灵感的表述还很多,诸如“天机”、“感兴”、“神思”之类的,但最具代表性并且能与西方灵感说并驾齐驱的还是“妙悟说”。
先来看看“妙悟说”的发展渊源。“妙悟”又称“禅悟”,来源于佛教禅宗的一个重要范畴。“禅悟”的基本要义就是“识心见性,自成佛道”。(《坛经》)并最终达到一种虚静清远、空灵清澈的精神境界。“妙悟”一词最早见于东汉曾肇的《长阿含经序》:“晋公姚爽质直清柔,玄心超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但此时“妙悟”只是在魏晋南北朝佛教领域内使用。 “妙悟”的灵感说形成时期是在南宋。南宋严羽所著的《沧浪诗话》对“妙悟”说赋予了新的内容,并成为“妙悟”说成熟的标志。严羽提出“入神”和“悟入”,他认为艺术的“悟”有如“禅”之“悟”,他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3](11―12页)严羽的“妙悟”说强调诗歌艺术的奥妙既非理论所能阐明,也非语言所能表述,要凭借直觉思维与心灵去体悟,诗家的妙悟和禅家的妙悟具有内在一致性。由此可见,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中的灵感说的产生就与佛教禅宗是一脉相承的。
再观西方灵感说的发展渊源,“灵感”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它在希腊原文中的意思是“神的气息”,用在诗人或艺术家的创作上,是指感受神的灵气而代神立言。他们得到神灵凭附,在创作中就会具有一种超凡的艺术创造力。最早提出“灵感”说的是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他说:“荷马由于生来就得到神的才能,所以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伟大诗篇”,“没有一种心灵的火焰,没有一种疯狂式的灵感,就不能成为大诗人。”[4](35―36页)对德谟克利特的观点进行系统阐述的是柏拉图。他在《伊安》篇中提到:“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来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科里班特巫师们在舞蹈时,心理都受一种迷狂支配;抒情诗人们在做诗时也是如此。他们一旦受到音乐和韵节力量的支配,就感到酒神的狂欢,由于这种灵感的影响,他们正如酒神的女信徒受酒神凭附,可以从河水中汲取乳蜜,这是她们在神智清醒时所不能做的事。抒情诗人的心灵也正像这样的,他们自己也说他们像酿蜜,飞到诗神的园里,从流蜜的泉源吸取精英,来酿成他们的诗歌。他们这番话是不错的,因为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神明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代神说话。”[5](8页)柏拉图认为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是诗人在神灵附体时创作出的,诗人在神灵的感召下,在追求真正的智慧时,获得艺术灵感,才能展开想象的翅膀,进行艺术创作。这不是普通的技艺所能企及的。后世把柏拉图的灵感说概括为“迷狂”说,具有两个特点:灵感是获得神灵的启示和感召,在追求智慧的过程中产生;诗人在艺术创作中处于迷狂状态。我们发现,古希腊的灵感说都带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柏拉图的“迷狂说”更是加强了诗歌创作的神秘性,并影响了整个西方灵感说的发展,长期在欧洲盛行,但灵感说的神秘色彩随着历史发展逐渐减少了。黑格尔在《美学》著作中也谈到:“想象活动和完成作品技巧的运用,作为艺术家的一种能力,单独来看,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灵感。”“灵感就是这种活跃地进行构造形象的本身。”[6](363―364页)在黑格尔看来,灵感是一种艺术家的能力,包括想象力与创造力,它的神秘色彩已经淡化了很多。
在对中西不同的灵感说渊源梳理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了中国的“妙悟说”和西方的“迷狂说”的发展渊源都与宗教有一定联系,且有以下共同点:
第一,两者都具有共同的灵感说特征:首先,灵感都具有突发性,它总是在艺术创作中不经意地出现,不是作家能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其次,当灵感到来之时,作家处于一种迷狂紧张的精神状态之下,作家的意识似乎不再受理智的支配,任凭“下意识”的推动,其才智似乎超出了平时的能力;最后,灵感到来之时,作家就会文思泉涌,创作得心应手,各种意象都会纷至沓来,作家如获神助,具有巨大的、雷鸣电闪似的综合创造力,许多流芳千古的绝世佳作由此诞生。
第二,无论是西方的“迷狂说”还是中国的“妙悟说”,它们的发展渊源都来自于宗教,与神有一定的关系。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出“入神”和“悟入”,认为艺术的“妙悟”与禅家的“禅悟”有着内在一致性。明清之际的陈宏绪也强调禅悟与诗悟的相通点,认为两者都表现人类最普遍的情感如悲悯情谊等方面是相通的,赋予妙悟说以宏阔的眼光。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中也有文章“通神”的论述:“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闲情偶寄》卷三)而柏拉图则认为诗人的灵感来自于神力,诗人是神的代言人,把灵感看作是“神性的着魔”,有幸获得灵感的诗人是“着魔于神的人”,能凭借神力创造出不朽的诗篇。由此可见,“妙悟说”和“迷狂说”的灵感论都呈现出与宗教紧密的联系,尽管各自的内容不尽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不容忽视:在文学创作中灵感闪现的非自觉,突发状态与进入宗教的不自觉思维状态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尽管“妙悟说”和“迷狂说”都与宗教思维有联系,但是它们各自受的宗教思维的影响以及它们呈现的状态与特点却有巨大的差异,并且这一差异性还取决于中西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哲学底蕴。我们在第三部分还会进一步论述。
通过第二部分对“妙悟说”与“迷狂说”的相同点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对其差异性进行分析与论述。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哲学背景决定了其不同的思维方式。分别代表中西诗学灵感论的“妙悟说”与“迷狂说”也不例外。西方世界是一个宗教性与商业性融合的社会,西方文学艺术的发展也自然打上了宗教的印记,可以说西方整个文化传统一直存在神性的维度。在古希腊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迷狂说”深远的文化根源,《荷马史诗》中的呼告诗神缪司和酒神祭者的兴诗,阿波罗的神谕等都从不同角度暗示灵感来自“神力”。柏拉图的“迷狂说”正是植根于这一文化土壤,并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而中国作为一个宗法制国家,更注重达到情理平衡以获得社会性、伦理性的满足,追求一种禅定虚静,静中体悟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中国灵感论“妙悟说”也是与这种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正是中西不同的文化与哲学背景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灵感论,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差异:
第一,“妙悟说”与“迷狂说”具有不同的哲学与美学内涵。“妙悟说”来源于佛教禅宗的“禅悟说”。“悟”是佛教禅宗的“终极话题”。“悟”是禅的灵魂,禅的生涯始于开悟之处。尤其在南宗思想中,强调与日常生活本身保持直接联系中当下即得,在四处皆有的现实境遇中悟道成佛。在日常普通的感性体验中可以超越,“妙悟”,以获得永恒不灭的佛性。在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中,“悟”也是个十分重要的美学概念。“悟”作为一种直觉,是刹那间获得的个人体验,是基于本觉直性的一种直观,消融于自心的体悟,具有深厚的宗教哲学思想与美学意蕴。诗学视域下的“妙悟说”沿袭这一美学传统而来,将禅悟融入诗心,使诗心与禅境合一;将具有禅学智慧的悟用于文学艺术创作中,体现出理性与直觉的结合。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提到:“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3](26页)他认为诗歌有特别的趣味,并非空洞的说理与议论就能成为诗歌。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诗歌理论是“不涉理路”的,他的诗禅学理论体系中以“妙悟”为中心分别阐述了“识”、“第一义”、“顿门”等五个基本要点,其中“识”即为理性认识,指佛学的“顿门”与“透彻之悟”。可见,“妙悟说”在深厚的佛教禅宗美学背景下,包含了禅学的理性智慧与直性体悟的思维方式,并内化为中国文学艺术创作思维与精髓。
再来看看柏拉图的“迷狂说”。众所周知,“迷狂说”的哲学前提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柏拉图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才能代表真理。而人只有依靠“回忆”,进入“迷狂”的状态,才能见到真理。柏拉图提出了回忆说,他认为回忆是灵魂对理念世界的渴慕与返回,是人回到理性家园的中介。在他的《会饮篇》中,柏拉图描绘了灵魂回忆“美”本身的过程,这是个从个别到一般,最后上升到美的理念的过程,同时也是灵魂不断上升,返回自身,回到理性家园的过程。迷狂则是灵魂在进行回忆时的一种极端亢奋的心理状态,在看到美本身的瞬间,心中荡漾的虔诚,情绪的高热与激动内化为诗人的创作灵感和冲动。这是一个生命摆脱肉体束缚,灵魂高飞远举的过程。看到理念世界的美,回忆起生前观照美的喜悦,对着理念的“影子”油然而生的眷恋,摆脱各种束缚,这就是一种迷狂的状态。但是,这种境界并非是丧失理智、陷入激情不可自拔,而是由于热爱智慧而摆脱世间束缚,进入凝神观照,超然物外的状态,创作的灵感油然而生。是故,“迷狂说”的本质并不是非理性的,只有哲学家和天才型的诗人才能进入迷狂状态,达到绝对的美的境界。柏拉图的“迷狂说”并非否定理智,而是否定人类自以为是的知觉、意见而追求更高的绝对的智慧。在此哲学与美学前提下,那些认为柏拉图的灵感论“迷狂说”具有非理智性,完全否定理智的说法自然是不攻自破了。我们不能仅停留于柏拉图的“迷狂说”中灵感的产生来自于神灵的附体的肤浅表层理解,还应该结合柏拉图深刻的哲学思想进行分析与研究。由此可见,中西不同的哲学与美学内涵造成了中西灵感说本质的差异性。
人生感悟和哲学 第3篇
我以《人生》这篇课文的课堂教学为例,进行了实践探究,尝试从这几个方面来确定教学内容:
一、细读文本,认识生活
接着,我让学生结合自己曾经的攀登经历,谈一下这里的“攀登高塔”有哪些特别之处。学生开始细读文本,结合课文内容,回答如下:
学生1:“这座高塔是中空的。如果人到达它的顶端,就会掉下来摔得粉身碎骨。”说明攀登的过程很难,不易到达目的地。
学生2:登塔的阶梯随时都可能从脚下消失。这种攀登是危险的,有不确定性。
至此,我发现学生已经完全读懂了课文前四段的内容,并借机进行深入引导,转入文本阅读的第二个环节。
二、多元解读,感悟哲理
人生感悟和哲学 第4篇
一、披文入情,体会情感美
诗是诗人“情动而辞发”的产物。在教学中,运用生动形象的电教手段,创设一种与诗相应的情境,就会使学生披文入情,缘情融情,感悟一切景语皆情语。
1.借景引情。在古诗中,诗人常常把自己的情感融入所描绘的景物之中,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孟浩然的《春晓》一诗,句句写景,字字含情,诗句看似写景,实为抒情,情景交融,达到情景一体的境界。我引导学生由景入手,从字词的理解以及再现诗的画面,体会诗人如何描写“啼鸟”“风雨”“落花”等景物,再借助多媒体课件,引导学生体会诗中“不觉”“知多少”等字词的情感色彩,从而把握诗人爱春、惜春的深情。
3.借读引情。古诗的情感常常蕴含在富有音乐美的语言之中,只有通过反复朗读、吟唱才能入境、察情。因此,我教古诗,总是把朗读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始终。起始阶段齐声读,个别读;深入学习阶段,边理解边朗读;学完全诗后,让学生反复朗读,或一唱三叹地吟读,或摇头晃脑式地自由读。总之,要让学生读得琅琅上口,滚瓜烂熟,声情并茂。
二、启发想象,领悟意境美
如《寻隐者不遇》一诗,语言十分精炼,初读此诗,似觉平易,细加欣赏,则易中有难。寻隐者来去过程,一字未提;与童子会晤时的寒暄和问话,也一概从略;童子答问也当不少,但诗人仅摘三句,答问不多,但寓意深刻。在教学中,我首先指导学生弄清诗的大概意思和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展开想象:“诗人在松树下问些什么,诗中有没有写?你能根据童子的回答展开联想补充出来吗?”“假如你是书童,你会怎么回答?”然后,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对这些问话一一作答,并让学生分角色当堂进行对话表演。在表演中学生思维活跃,想象丰富,对答如流,还伴有生动、有趣的动作表演,把《寻隐者不遇》一诗中的寻访场面生动地再现出来,初步领悟到诗的意境。
三、读诗作画,再现画面美
画家用线条、颜色表示形体,诗人则用语言来绘色绘形。高超的“画笔”,可使“画中有诗”,而美妙的“诗笔”又可使“诗中有画”,从而使得诗情画意融为一体。我抓住古诗“诗中有画”的特点,把“诗”与“画”结合起来进行教学,通过作画,具体而形象地再现古诗中的画意,唤起学生丰富的联想,从而引导他们深入体会古诗的画面美。读诗作画,我经常采用以下几种形式:
1.教师作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根据诗意,用简笔画的形式,一次性或逐步呈现诗的画意,帮助学生感受诗的画面美,加深对诗的理解。如在教学《小儿垂钓》一诗时,我将一幅小儿垂钓图用简笔画勾勒出来,展现在学生面前,在观察图画的基础上,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理解词语,理解诗句。诗画结合,一个天真活泼、聪明伶俐的儿童形象,在学生的心目中就活起来了。
2.师生同画。在初步了解诗意的基础上,教师和学生共同作画,把诗人的语言变为直观的画面,理解诗的画面美。如《望庐山瀑布》一诗的教学,师生分三步读诗作画:第一步,在解题时,我边讲边画出诗人李白仰望瀑布的简笔画,让学生一开始就进入诗境,在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形象。第二步,读完第一、第二句诗后,我让学生想象诗的意境,添画“香炉峰”“生紫烟”“瀑布挂前川”,突出瀑布的背景美。第三步,读三、四句诗后,为了突出“飞流直下”的气势,我在学生画的瀑布上用粉笔横着由上往下添上有力的几笔,让学生感受瀑布的动态美。
3.学生自画。在教学中,我常常引导学生在把握诗意之后,展开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画面,再独立地画出诗意。如《寻隐者不遇》一诗中的“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一句,是童子回答来访者的话。为了让学生体会“云深”一词所描绘的意境,我让学生展开想象:“假如你是寻访人,当你顺着小书童的手向大山方面望去时,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学生纷纷回答:“我看到的是层峦迭嶂,云雾缭绕。”“我看到的是山高林密,路转峰回,云缠雾绕。”接着我让学生自由作画。有的学生画了一座大山,山中有大团的云雾;有的画上小房子、青松、寻访者、小书童。学生越画兴趣越浓,对诗中的画面美有了深刻的感受。
四、探求意蕴,理解哲理美
古人在进行创作时,往往把自己的情操、理想等融入景物描绘之中,或让人受到激励,或使人受到启发,从而赋予诗歌蕴含深刻的哲理。根据哲理诗的特点,引导学生品味古诗的哲理美,教师在教学中应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1.情与理。哲理诗中的“情”与“理”,是诗人的情感与理性观念的对立统一关系。不少古诗往往通过抒情而言志,情中有理,理中含情。如李绅的《锄禾》一诗,不仅抒发了诗人同情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感和无限的愤慨,而且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劝戒世人珍惜粮食,珍惜农民的劳动。教师在教这首诗时,不但要引导学生感悟诗中的感情,还要体会诗中情理交融的哲理美。